论北魏佛教的几个特点
发布时间:2023-01-19 15:40:03作者:楞严经入门网论北魏佛教的几个特点
业露华
佛教传来中国,始于汉代。但在汉魏之际,佛教只是作为神仙、方术一类的东西,被宫廷和一些上层贵族祭祀,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除了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僧人以外,汉人出家者极少。及至魏晋,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佛教的教义、思想逐渐被介绍过来,同时由于魏晋玄学的兴起,大乘佛教般若思想与魏晋玄学相结合,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中间佛教开始流行起来。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两地的社会情况不同以及思想、学术传统区别,流传于南方和北方的佛教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南方佛学继承了魏晋遗风,崇尚于义理的探究。玄学与佛理相融,名士与高僧交流。本末、有无之争,因果、形神之辨,是南方佛教界经常论争的问题。北方佛教则受频繁活动在河北、凉州等地的佛图澄、道安、昙无谶等僧人的影响,崇尚宗教实践,注重修行。因此,禅学与净土流传较广,而且不计工本地造寺建塔、开窟凿像,大兴土木以期多植福田,广建功德。
唐代僧入神清在谈到南北朝佛教时说“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许多前辈学者亦曾多次论及此期南北佛教的各自特点,如吕激先生曾言:“概括地讲,南方佛学偏重于玄谈,北方佛学偏重于实践。因此义学在南方比较发达,禅法在北方广为流行。”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写道:“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
这些分析,对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是很有启发的。这儿想仅就北魏佛教的特点谈一点粗浅的看法,由于个人的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还求诸位多加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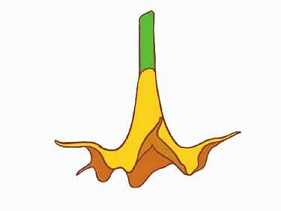
一、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
公元386年,拓跋硅即代王位,接着改国号称魏,389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即魏皇帝位,正式开创了北魏王朝。拓跋硅凭借武力先后攻取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邺(今河南临漳县)等地,及至其孙太武帝拓跋焘于436年和439年分别灭了北燕和北凉,北方中国基本上被统一。在北魏皇朝统治的一个多世纪中,北方中国的佛教得到了惊人迅速的发展。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时,全国有寺院六千多所,僧尼七万七千多。到了北魏末期,全国已有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共二百万了。
北魏佛教如此兴盛,发展如此迅速,这是与北魏国家政权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而北魏佛教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的色彩。由国家政权建立各级僧官机构,任命各级僧官,通过各级僧官直接控制全国的佛教徒。
早在北魏建国之初,就开官设置僧官了。据《魏书·释老志》记,太祖道武帝时,赵郡有沙门法果,精于修行,持戒严格,善于讲道。太祖闻其名,诏徵京师、后被任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此是北魏设僧官之始,后来,沙门师贤、昙曜等曾先后担任道人统(沙门统)之职。
北魏管理僧务的机关,初名“监福曹”,后改称“昭玄寺”。昭玄寺“备有官属,以断僧务”。此外,各州、镇、郡设有维那、上座、寺主等各级僧官。这些中央和地方各级僧官和管理僧务的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完整的僧官系统。这个僧官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央政府统辖之下管理全国僧徒,具体处理有关僧务,包括制定和执行僧律,决定和批准僧籍,掌握掌理僧祗粟等。北魏国家政权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僧官体系来控制和管理全国佛教徒的。僧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说明了北魏政权正式承认了佛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表明北魏佛教一开始就具有国家宗教的倾向。
北魏佛教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的另一个表现,是国家直接赋予佛教“巡民教化”、“敷导民俗”、安抚民众的任务。
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中国长期陷入了混战之中。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发动战争,互相残杀,给中原地区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鲜卑族的拓跋部落就在这战乱中乘机而起,逐渐强大起来。他们凭借武力,不断兼并别国,逐步统一了北方。但是,要维护和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光靠武力征服是不行的,还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强化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控制。因此,北魏统治者不断吸收当时比较先进的汉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学。太祖道武帝时就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世祖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年)于平城之东别起太学,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诏王公以下卿士、子息皆人太学。此外还任用汉人担任官吏,采取一系列措施加速拓跋部落的封建化进程。后来孝文帝又进一步进行改革,促使鲜卑族汉化。除了采用儒家思想作为指导国家政策的基本思想之外,早已在这一地区流行的佛教,亦是北魏统治者加以利用的一个思想武器。
黄河流域地区本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魏晋以后,佛教在这一地区也很流行。著名僧人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等曾长期在这一地区活动,他们拥有广泛的信众,形成了一些有势力的佛教僧团。如《高僧传》记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译经时,曾聚集义学僧人八百人之多。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也引起当时北方各国统治者的重视,受到尊崇,经常参与军国大事。北魏所经略的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他们选择佛教作为教化、安抚这一地区的民众是顺理成章的。
拓跋族的先祖曾对佛教略有接触,据《释老志》记:“文帝(沙漠汗)久在洛阳,昭成(什翼犍)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武帝攻略黄河北岸时,所过僧寺,对沙门表示礼敬,并令军队不得侵犯。太宗拓跋嗣则“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从此,国家政权正式赋予佛教巡民教化、敷导民众的重任。
北魏佛教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的特点,还表现在国家直接对僧务的干涉。这一干涉包括国家控制僧尼资格的批准权,经常对僧尼进行简别沙汰、直接干预僧律的制定和执行等等。
僧尼出家,要得到批准,才能具有僧尼资格(僧籍)。这一批准权,主要由朝廷控制。高宗文成帝复兴佛法时,魏帝曾亲自为师贤等人剃发,并下令诸州“好乐道法,欲为沙门者,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以后历代魏帝均有度僧之举。如高祖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八月,在永宁寺“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至太和十六年(492年)又令“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
朝廷如此奖励出家,扶持佛教发展,致使僧尼队伍不断庞大,从而导致清浊混流,精粗莫别。因此,政府又得出面进行控制、简别。北魏时期,曾多次发生沙汰沙门之事。太武帝平凉州后,迁移凉州居民至平城,致使“象教弥增”,不久即以沙门众多,“诏罢五十已下者。”延兴二年,高祖孝文帝下令对无籍僧尼“精加隐括”。太和十年(486年),又因“愚民侥幸,假称人道,以避输课”,命令严加清检,罢遣无籍僧尼,并命令各地寺主维那进行审核,凡是不合条件的一律取消僧籍。至熙平二年(517年),朝廷再次重申控制度僧,对僧尼的资格,各地度僧的人数等都有具体的规定,但由于此时已“法禁宽褫”,因此未能切实贯彻。
僧律,本是佛教对其信徒在日常生活、宗教仪式、宗教修行等各方面作的规定。佛教传来中国后,中国的僧徒们也曾按实际情况制定过一些僧律。北魏时,政府曾出面先后数次制定“僧禁”。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还亲自命令沙门统僧显修立僧制四十七条,以“设法一时,粗救习俗”。所有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北魏佛教是在北魏政权的严格控制下发展的,是具有鲜明的国家政治色彩的宗教。这种情况与江南佛教有很大区别。
晋室东迁,中原士族相继来到江南,东晋政权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士族豪门势力在江南仍然保持强大的力量。整个南朝时期,虽然皇权迭经变动,但豪门世族的势力没有根本触动。软弱无力的南朝国家政权无法控制同世族名门关系密切的佛教界。南朝时虽亦多次提出精简沙汰沙门,发起要求佛教界对王者礼拜的讨论,但终因无力实行,加上一部分世族出身的奉佛者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北魏政权则是一个新兴的封建贵族集团。自太武帝“分土定居”,奠定了北魏封建化的基础,后来孝文帝改革,强化了北魏的封建统治,在这一进程中,皇权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因此有能力,有力量对佛教加以控制。而且,由于佛教在北魏境内的发展,使国家觉得需要对佛教进行控制,这样,就促使北魏佛教形成国家控制宗教的特点。
从佛教方面来说,由于战乱,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需要依靠一个强而有力的势力保护。晋代的释道安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北魏佛教正是实践了这一条道路。首任沙门统法果紧紧依靠国家政权,为了佛教能在北魏境内顺利地发展,他公开要求佛教僧徒礼拜北魏皇帝。《魏书·释老志》载:“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
按印度佛教习俗,沙门出家,不礼世俗之人,无论是帝王还是父母,一概不拜。因此,僧徒礼拜王者显然不合佛教教义。法果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提出魏帝“即是当今如来”的说法,他还对人解释,我并不是拜天子,而是在礼拜佛啊。
如果我们拿江南佛教情况与之进行比较,那是很有意思的。与法果几乎同时的、活跃在江南庐山的沙门慧远(334—416年),恰恰是在关于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的问题上,与法果的态度截然相反。东晋末年,太尉桓玄为了“尊主崇上”,召集属下官吏进行讨论,要求沙门必须礼敬王者。慧远为此而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详细论述了他所认为的出家人不应礼敬王者的道理。他坚持主张沙门出了家,是世外之人,故不应以世俗的礼法来要求。也不应以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慧远不畏权势,敢于同有“震主之威”的桓玄极力抗争,在江南佛教界获得了极大的尊敬。
佛教是一种宗教信仰,但是,佛教徒,包括出家的僧尼在内,首先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必然会遇到许多现实问题。当宗教信仰与现实利害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适当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要符合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情况。同是关于沙门敬王的问题,在南北两地就因为社会条件不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北魏王权强而有力。因此佛教不得不紧紧依靠世俗的王权。把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作为现世如来,从佛教来说,这也是出于一种生存需要。北魏佛教发展如果一旦与国家政权发生矛盾,政府就会运用行政力量加以干涉。如对僧尼们限制沙汰就是这样。这种干涉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太武帝灭佛那样的激烈事件。整个北朝在不长的时期内,接连发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二次灭佛事件,不能不说这是与当时北方的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控制有关。
江南由于王权孱弱,佛教在世族豪强的支持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江南佛教,基本上限于理论上的争论,而于行政干涉之事极少发生。就如梁武帝欲以帝王之尊驾驭僧官,拟自任“白衣僧正”,而开善寺智藏则公然表示反对,声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武帝亦无可奈何而罢白衣僧正之议。因此,从佛教与国家政权关系这一角度,将江南河北两地佛教情况对比,可清楚地看出北魏佛教一开始就有着国家宗教倾向。
二、佛教流传的普遍性和民众性
北魏佛教既然担负着巡民教化、敷导民俗的任务,那么必须在普通的民众中间开展广泛的活动。因此,佛教流传的普遍性和广泛的民众性,亦成为北魏佛教的一个特点。
江南佛教崇尚义理,当时世风又雅重清淡,因而文人学士、士夫望族等均于释氏有交往。名士如何尚之、宗炳、谢灵运、周颐等,不仅与当时一些著名僧人关系密切,而且他们本人也都写过许多阐述佛学义理的精彩文章,显示了他们对佛学理论的深刻见解。正因为偏重义学,偏于理论的探讨,因而谈玄说佛成了一些贵族士大夫等有闲阶级的精神消遣。名士与高僧结交,成了一时的风尚,广大下层民众则无缘,也不可能跻身其间。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江南佛教基本上是贵族、士大夫的宗教。
北魏佛教并不注重虚玄高深的理论研究,它重视的是宗教的修行实践。因此简单易行,没有许多繁文琐义,容易为一般民众接受,可说是一种民众的宗教。故而北魏时期佛教流传的面很广,上至皇帝宗室、官宦贵戚,下至里巷平民,均有崇佛者。
北魏佛教广泛流传的情况,从北魏都城洛阳四月八日行象之盛况中也可看出。
传说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诞生于四月八日,《法显行传》及《南海寄归传》记:佛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释迦去世后,后人恨未能亲睹真容,故于每年此日立佛降生相,或太子巡城像,载以车辇,周行城市内外,受众人之瞻仰礼拜,称为“行象”。用以表达对佛的景慕虔诚之意。北魏时亦有这一风俗,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行象之前,京师诸像都要会集景明寺,共有一千余躯之多。伴随着行象出行,要举行盛大的宗教庆祝活动。《洛阳伽蓝记》卷一“长秋寺”条记寺有一六牙白象负释迦像,像出之时“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族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卷二“宗圣寺”条记寺有像一躯高三丈八尺,“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辉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行象之日,千余躯像依次进入宣阳门,来到皇宫前,魏帝在门楼之上散花礼敬:
“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
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此。名
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
繁衍相倾。时有西城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
一派热闹欢腾的气象,说明了北魏佛教不只是流传于宫廷贵族之间的上层社会的宗教。而是广泛流传在社会的民众的宗教。《洛阳伽蓝记》所记北魏洛阳城内的寺院,除皇亲贵戚、达官贵人所建之外,还有一些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平民所立的,如灵应寺、开善寺、归觉寺等。特别是归觉寺,据记载是由屠夫太常民刘胡舍宅为寺所谓“太常民”,即隶属于太常机构的杂户。“太常”所属应是乐人,但其中也有管理祭祀牲畜的廪牺署。刘胡其人即是在这一部门中服役的杂户。所以习于屠宰。其地位当在奴婢之上、平民之下。另外,《洛阳伽蓝记》卷二“璎珞寺”条记建阳里内有士庶二千余户,“信崇三宝”,供养着附近十个寺庙的人僧众。
从身操屠宰之业,社会地位低下的太常民刘胡舍宅为寺,以及建阳里士庶百姓供养十寺僧众这些事实来看,北魏佛教在一般民众,特别是社会下层人民中间已有很深影响了。
北魏佛教具有如此的普遍性和民众性的原因,除了北魏佛教本身不重虚玄难懂的教理、比较简单易行之外,还因为:
第一,北魏佛教接受了敷导民俗的任务。因此,它必须在民间“巡民教化”,在下层民众中广泛开展传教活动。
第二,北魏统治者大力宣传、扶持。他们广度僧尼,到处造寺立像,及至不惜工本。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凿石窟,等等,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
第三,由于长期的战乱,民无宁日,他们极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不到,他们就转向对来世的追求。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九的《北魏造像诸碑总论》中,论及北魏时期人们普遍信仰佛教的原因时说:“尝推其故,盖自典午之初,中原板荡……民生期间,荡析离居,迄无宁宇。几有‘尚寐无讹\’、‘不如无生\’之叹,而释氏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上升兜率天宫之说诱之。故愚夫愚妇,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余年来,浸成风俗。”而且,出家为僧,又可避交租税力役,因此,当人民不堪忍受沉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时,就相继人道,躲进寺院的庇护之下,甚至有绝户为沙门者。
第四,人民的反抗,又往往以佛教为幌子。北魏时期的沙门造反,见于史籍所记载的,从孝文帝至宣武帝的四十余年中,就有八次之多。一些沙门利用佛教号召组织民众反抗政府,在客观上促使佛教在下层民众中迅速流传。
总之,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形成了北魏佛教具有广泛的民众性这样一个特点。
三、佛教与巫祝神咒的混合
北魏佛教既然流传普遍,具有广泛的民众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和早已在民众中流行的原始宗教迷信相混合,所以大量掺杂有巫祝、神异、灵验、咒术等类东西,是北魏佛教的另一特点。
据《洛阳伽蓝记》卷二“平等寺”条下记,寺门外有像一躯,“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详异。”卷四“白马寺”条下记“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丑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谶,不可得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还有,卷四“法云寺”条下,记西域沙门昙摩罗“秘咒神验,阎浮所无。咒枯树能生枝叶,咒人变为驴马,见者莫不忻怖。”
这些说明了当时北魏佛教是伴随着巫祝神咒等神仙方术之类的东西而流行的。
汉时佛教传人中国,当时人们将之视为祠祀的一种,认为佛教讲精灵不灭、主张炼形炼神,白日飞升。当时佛教与神仙方术相结合而流传。魏晋时期,佛教教义逐渐与中国哲学唯心主义相结合而显出其理论特色,但另一方面,其宗教迷信方面的东西,也和中国本来就有的巫祝筮卜、谶纬神学等东西进一步相结合而在社会上流行。例如晋永嘉年间来洛阳的、后被石勒、石虎两代奉为大和尚的西域僧人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燕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还能“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活跃在凉州一带的沙门昙无谶,曾与智嵩等译出《涅檠》诸经数十部,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他同时又是个“晓术数、禁咒”的异僧。魏帝曾“闻谶有道术”而派人迎请,北魏佛教直接受到河北、凉州一带佛教的传承和影响,因此自然大量掺有巫祝咒术一类的东西。
另外,北魏先世起自漠北,原先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部落,其文化程度比之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族文化相去甚远。由于其本身文明发展程度低,因之在吸收佛教这样一种宗教思想文化的时候,容易对其中迷信方面的东西发生共鸣,所以相对于佛教教理学说而言,更容易接受那种咒术、灵验一类的东西。不仅北魏如此,十六国时期都是这样。例如佛图澄,主要就是靠了道术、咒语一类东西来传播佛教的,《高僧传》记其劝化石勒之事,先是依靠预卜吉凶,后石勒召见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石勒“不达深理”,因此表演了一套咒术,“勒由此信服”,而且后来使得“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但这些人是否都对佛教教义真正理解呢?看来并非如此,“国人每共相语,莫起恶心,和尚知汝。”说明他们畏惧的是佛图澄的道术。
北魏佛教的产生和发展,与太祖道武帝和太宗明元帝极有关系,他们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制定了令沙门“敷导民俗”的政策。但他们是否对佛教教义真正理解呢?据《魏书·释老志》言,太祖“好黄老,颇览佛经”。而太宗则是“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其实他们并不明白黄老与佛法之间的区别。魏太祖在征战中,为想取得隐居泰山的名僧僧朗的帮助,曾致书僧朗,其中称赞僧朗是“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天兴元年,太祖下语论及佛法,认为是“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说明他们只是将佛教作为神秘的东西而表示敬畏,或者是为了世俗的福事而进行祈求。
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曾一度毁佛之外,大部分都信奉佛教。但真正对佛教理论有兴趣的,唯有高祖孝文帝及世宗宣武帝,史书记孝文帝曾命人讨论佛义,他自己喜好《成实论》,认为可以“释人染情”。宣武帝则“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纶,广集名僧,标明义旨”。因此,北魏佛教直到孝文帝之后,义学才真正有所发展。孝文之前诸帝,尽管他们也信奉佛教,但很难说他们在佛学方面有什么造诣。如一度废佛的世祖太武帝,起先也曾“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且还“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他终究是“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自世祖太武帝起,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要到道坛亲受符录,以表示对道教的信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与巫卜神咒一类的东西混杂流行,是不足为奇的。
再看一下北魏建国初期的佛教界情况,最早的几任沙门统是法果、师贤、昙曜。法果曾把北魏皇帝称为“当今如来”,公开号召沙门要对之表示礼敬,因而深得太祖、太宗的赏识,封以高官厚禄。师贤、昙曜二人均是从凉州到平城的,无疑会带来凉州佛教的影响。昙曜从中山赴平城时,还有“御马衔衣”之兆,可见巫卜灵验等迷信与北魏佛教关系之深。沙门统昙曜曾参与组织佛经翻译。据《历代三宝记》载,昙曜曾译《付法藏传》等经,这是因为他“慨前陵废,欣今载兴。故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庶使法藏住持无绝”。由此,从北魏前期担任佛教界领袖的几位僧官情况看,他们并非是在佛学理论方面有所研究发展的义学高僧,而是担当了处理和协调政府与佛教界之间关系的中间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佛教在北魏境内的生存和复兴,而不是佛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佛教的义学发展不快,而宗教迷信方面的东西却混合着巫卜神咒等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魏晋时期的思想学术以研究三玄为主,晋室东迁,南朝基本上继承这一思想传统。老庄思想与般若学说相融合而流行,儒家学者则常常作为佛教的对立面出现。北朝经学却常和佛教发生关系,北方儒家孙惠蔚、刘献之等,都与佛教关系密切。前者曾与魏帝夜论佛经,颇合帝意,故赐字“惠”,世称惠蔚法师。后者曾注《涅檠经》未就而卒。魏之大儒徐惠明弟子卢景裕好释氏,通大义,世称居士。因此菩提流支译经论请景枯作序。菩提流支门下道宠,初名张宾,亦是儒者。慧光的弟子慧顺是侍中崔光之弟,崔光为国子祭酒,同时著《维摩》、《十地经论》义疏三十余卷。另外,重视禅法的僧稠曾是太学博土,等等。如此儒佛交流,必致交互影响。而北魏经学,上承汉末,好谈天道,杂以谶纬,因此,北魏佛教掺杂有巫卜神咒、阴阳术数等,亦是汉代佛教附庸神仙方术、阴阳术数的余绪。
综上所述,北魏佛教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它在一般民众中,特别是在社会下层群众中流传极广;掺杂有大量的巫卜神咒,谶纬灵验,阴阳术数等宗教迷信。除此以外,北魏佛教还非常重视宗教实践,崇尚禅学、戒律等。因此,当时北方禅学、律学和净土等较为发达。释玄高为佛陀禅师门下弟子,沙门统昙曜“以禅业见称”,《洛阳伽蓝记》卷二记当时“京师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说明了北魏禅法之盛况,而《僧祗》、《十诵》、《四分》等律学在北魏时也很流行,及至后来北齐慧光成了《四分律》之祖。宣传净土信仰的昙鸾亦活动于北魏一带,等等。所有这些,许多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总之,北魏时期的佛教有许多与江南佛教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情况不同、佛教发展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的差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研究北魏时期佛教特点,有助于我们对整个北魏佛教史乃至于整个中国佛教史的研究。



